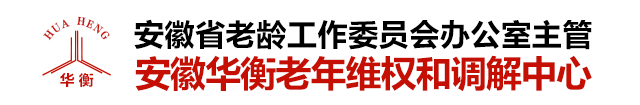“上海九旬老太遗嘱无效”案,完整裁判理由来了
近日,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审理的一起继承纠纷案件引发社会广泛关注,多家媒体进行了报道。
本案中,法官通过异地调查,抽丝剥茧还原事实真相,阻却了“干儿子”老刘欺诈取得遗嘱最终获取财产的目的。那么,这份遗嘱究竟为何被判定无效?法院的判决依据又是什么?来看看本案的裁判理由。
案情回顾
上下滑动查看更多
裁判理由
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系争代书遗嘱是否有效,老刘能否依该遗嘱取得遗产?二、老刘在王老太生前取走的钱款是否应作为遗产继承?
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法院认为,王老太在律师见证下订立的遗嘱,形式上符合代书遗嘱的法律规定,但遗嘱作为单方民事法律行为,其效力核心在于立遗嘱人意思表示的真实、自由,《民法典》第1143条明确规定,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结合全案证据及当事人陈述,法院认为,本案系争代书遗嘱是王老太在受到老刘欺诈的情况下订立,不能表示其真实意思,应认定为无效,理由如下:
首先,老刘存在虚构身份骗取王老太同情的行为。遗嘱见证视频显示,王老太两次向律师表达老刘16岁参军,系国际维和部队军人,一生走过70多个国家,名下没有房产,所以要把房产留给老刘,并称老刘不让其对外说这些情况。老刘辩称王老太的错误信息来自于他人而非自己,法院对此不予采信。即便如此,老刘在明知王老太受到误导的情况下对自己的真实身份负有披露、澄清的义务,故意隐瞒真实情况亦构成欺诈。实际上,王老太有着随解放军南下到上海、跟解放军学会了识字的经历,可想而知其对军人有着天然的好感和信任,老刘无中生有且如此精准地为自己编造了国际维和部队人设,其辩称没有欺诈恶意难以让人信服。同时,法院注意到王老太在回答律师有几名子女时,王老太回答有五名,并将老刘称作大儿子,其未必清楚“干儿子”并非法律意义上的“儿子”,律师出庭作证时称其不清楚老刘与王老太的真实关系,故未向王老太作相关法律提示。老刘作为主动联系律师的一方,应负有说清真实身份关系的义务,但老刘并未进行告知。
其次,老刘存在阻断王老太与家庭联系的行为。老刘将王老太带至山东农村,并更换了王老太的电话号码,同时拒绝小林及其他家属的联系请求(如不接听王老太侄子、侄女电话、拒绝小林多次添加微信的请求),使王老太处于人为制造的隔离之中,产生只有老刘可以依赖的错误认知。王老太对律师称“其他子女都不管我”“他们都不来看我”,并称大林是在立遗嘱当年(即2023年)刚去世,而实际上大林早在2020年就已去世。从王老太的视角来看,子女中与其关系最好的大林亦是多年对其不管不问,且王老太并不知道孙子小林在寻找她。而这些错误认知与原告的隔离行为密切相关,直接影响了王老太对其他亲属的判断。
再者,老刘的欺诈、隔离行为与遗嘱内容有直接关联性。从王老太与律师的谈话中可以明确得出,其作出遗嘱处分主要基于两个原因:一是对老刘的认可和同情,二是对其他子女不孝的不满与惩罚,而这两点如前所述均受到了老刘的不当影响。尽管一般情况下动机错误并不影响意思表示的真实性,但本案中,王老太的动机内容在遗嘱订立过程中明确对外表达,已构成意思表示的组成部分,且该错误动机的形成应归责于老刘。如果没有老刘的欺诈、隔离行为,王老太极有可能不会作出如此处分。(大林去世前曾长期照顾王老太,包括安排王老太进养老院,王老太曾和小林共同生活,还作出过公证遗嘱要将系争房产留给小林。试想,如果王老太知道老刘编造身份对其进行欺骗,而孙子小林一直在寻找奶奶下落,是否仍会如此决绝地将全部财产赠给老刘?)法院认为,在遗嘱这类尤其强调表意人真实意愿的单方民事法律行为中,若动机受到欺诈等行为的污染,应认定遗嘱并非被继承人真实意思表示。
最后,老刘对王老太的扶养行为不构成合法抗辩事由。老刘在庭审中一再强调王老太“无人赡养”,其对王老太“用心照顾”,王老太对其“十分认可”,但即便如此,其行为本质仍属通过欺诈不当谋利。其一,王老太虽与另外三名子女关系不睦,但其养老事宜仍有小儿子大林负责,在大林安排下住进养老院,大林去世后小林也主动联系养老院拟接手王老太养老事宜,故王老太并非无人赡养的孤寡老人,是老刘的介入使王老太与家庭完全隔绝。其二,王老太是享受高额养老金的高龄老人,而老刘无稳定收入,在与王老太共同生活期间,王老太每月近万元养老金及20余万元定期存款积蓄均被支取殆尽,老刘称王老太的养老金未用于共同生活,法院不予采信,即使不考虑房产的遗赠,老刘在与王老太共同生活期间也获得了经济上的利益,实在难言纯粹的善意扶助。其三,从老刘在王老太去世前后的做法来看,更谈不上其所谓的“母子情深”,老刘在发现王老太昏迷后并未第一时间拨打120进行抢救,且在王老太去世后未联系其家属,在去世当日便将遗体火化并于次日将骨灰撒在了附近山上,老刘称系王老太的生前意愿,但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法院不予采信。老刘明知王老太有其他子女,作为一个理性的、王老太“信任”的人,应该积极劝和,至少在王老太病重期间、去世之后应该努力联系王老太的子孙,但老刘却没有做任何努力(王老太于2023年12月22日去世,老刘于2024年1月8日便委托了律师,于2024年1月26日签署了含王老太子女、孙子信息的起诉状,可见其并非不能找到王老太家属)。老刘在王老太去世后不通知家属、未办理后事、撒骨灰于山野的行为,违背人情伦理,更加凸显其假装“孝子”的伪善本质。法院认为,血缘关系并非扶养的唯一基础,老人的意愿应当得到尊重,法律规定了继承人以外扶养较多的人可以分得适当的遗产, 但前提应当是扶养人系出于善意、而老人的意愿是真实、自由的,本案中老刘的扶养是建立在违法行为的基础之上,法律不能因部分“表面善意”而容忍整体行为的违法性。
法院认为,赡养老人、孝敬长辈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但对老人的赡养必须以合法、正当的方式进行,通过欺骗诱导、藏匿老人等非法手段谋取利益的行为,不仅违反法律规定,更是对“和谐”“友善”“诚信”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严重背离,应受到司法裁判的严厉否定。
综上,王老太订立的代书遗嘱无效,老刘不能据此取得王老太的遗产。
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小林主张老刘在被继承人王老太生前从其名下账户领取的定期存款20余万元系王老太遗产,老刘在审理中曾称从未领取王老太钱款,后在法院出示银行签字底单后承认有20余万元从王老太名下账户转存至自己名下账户,并主张该钱款中包含了自己的收入且王老太明确表示将钱款赠与自己。法院认为,老刘未提交证据证明自己的收入,且无法说明具体数额,而王老太长期以来均有购买定期存单的理财习惯,故对老刘主张王老太定期存款中包含老刘收入的事实,法院不予采信。针对赠与事实,老刘同样未提供任何证据予以证明,且法院注意到,系争的定期存款转至活期账户后,系通过ATM机取现方式提取,因ATM机取款金额有限,取款人常连续多日分多笔进行取款,王老太如要赠与老刘钱款,完全可以通过转账或柜台取现的方式进行,通过ATM机取现20余万元进行赠与显著缺乏合理性,故对老刘主张的赠与事实法院不予采信。本案中,小林主张的20余万元仅系王老太定期存款部分,法院认为,王老太每月的养老金收入足以覆盖其日常开支,老刘称王老太养老金均用于服用药物或接济他人,但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也无证据证明王老太钱款有其他合理去向,故对小林主张老刘处尚有王老太遗留的钱款20余万元,法院予以采信,该钱款应作为王老太的遗产进行继承。
在厘清以上两个争议焦点后,法院对被继承人王老太的遗产作如下处理:
关于遵义路房屋,王老太另立有公证遗嘱,本案中并无证据证明公证遗嘱存在效力瑕疵,故应认定为有效,遵义路房屋应按照公证遗嘱由小林继承所有。
关于王老太的存款,因未发现有涉及存款部分的有效遗嘱,故应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本案中,王老太的法定继承人为王老太三名子女以及代位继承人小林,需明确的是,即使老刘与王老太结为干亲关系,亦非法定继承人,不享有法定继承权。本案中,根据查明的事实,王老太三名子女与王老太关系不睦,长期以来对王老太不闻不问,三人的行为已符合不尽扶养义务应少分或不分的情形,然而审理中小林明确要求存款部分由四人均等继承,并表示正在依习俗协调办理王老太衣冠冢落葬等事宜,法院从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及修复家庭关系的角度考虑,对小林要求均等分割的请求予以准许,但责令王老太三名子女深刻反省自身不尽赡养义务的行为,相互配合与小林共同处理好未尽的善后事宜。
综上所述,法院判决驳回老刘的全部诉请,遵义路房产判由小林继承,并判令老刘将王老太的20余万元存款交还。后老刘提出上诉,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25年7月31日驳回其上诉,维持原判。
免费咨询热线
专业客服为您解疑答惑